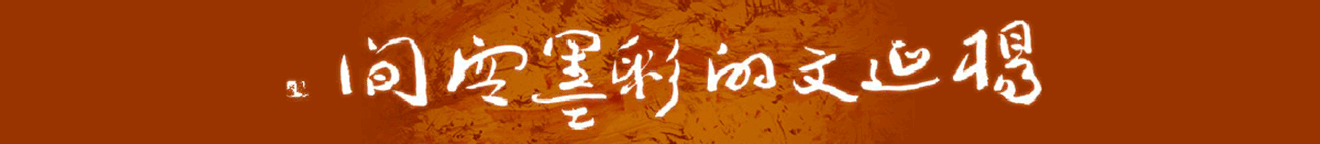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0/12/7 15:39:17 点击:1251
作者:康 征
以气韵、意境为审美内涵的中国画绘画和以色彩美、形式美为内涵的西方绘画成功地婚配且生下健康活泼的混血婴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自中西绘画有史交流以来,能够成为这一混血婴儿之父的艺术家寥若晨星,以我陋眼之拜观,卓然其间的不过林风眠、黄永玉、杨延文三人耳。林、黄二老早有公论,此不赘述,杨延文者,其色也达情,其墨也达韵,其笔也通神,虽生于二老之后,却凛凛处其间,飒然大家也。
走进中国绘画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包前孕后成一代大家者,莫不有极强的吸收力与消化能力,在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吸收与消化能力的培养更多来自对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前人文化艺术传统的精研与继承,首先便失去这种能力滋生的前提。当然,杨延文也不例外,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对中国诗歌、古典戏剧、文学和历史就特别地偏爱,这种最初的爱好和以后的磨砺使他的审美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日益丰富起来。当他脱壳于西方油画而走向中国画的创作时,他自信地说:“博大精深传统的滋养,使我有驾驭中国画的信心。”如果当初他就是一位国画家,靠他的智慧,他也许会在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吸收吐纳,在传统的山、水、云、树间寻找创造性的机缘,这样他也只能与同时代的画家比肩接踵。然而,他却从绘画高峰的另一个坡面攀登而来了,在北京艺术学院就学期间,他攻读的是油画专业,在他那个时代,卫天霖、吴冠中代表着西方绘画,特别是法国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和现代派绘画在中国的传播者,但同时在他们的绘画中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思想和民族性的绘画特征。就艺术的本源和绘画的审美情趣,杨延文登堂而入吴冠中之室,接受的正是这一艺术体系的绘画原理。另一方面,杨延文的成功还来自他坚毅而自信的性格,吴冠中曾称赞他的静物习作,“杨延文画画如60度的白干,60度就是60度!”我们由此亦可知他对艺术风格、技法的领悟已达到了尽精刻微的“纯度”。但他并没有由此而泯灭自己的个性,吴冠中先生赞赏他“执着与直率的性格,正是艺术追求的最好品格”。人体写生代表着作者综合性情绪和提炼综合的能力。最终在画稿上呈现出的还是作者的情感,如果拘泥于人体局部或整体的体位变化,那必将在被动的牵引中失去个性。因此,他的“执着”就是他的认识。是长期在中、西方绘画艺术天赋的碰撞、对抗、思索、交融之后的积累所达到的升华。
西方绘画重技重表,中国绘画重道重质。这大概是不可逾越的区别,以法国印象派为例,他们把描绘对象之大千世界,万物造化的生动与美,统归于光与色的作用,他们认为应该把光、色作为艺术家表现的目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光与色这些表现的描述支配着他们的情感和创作。1875年爱德华•马奈的风景画《威尼斯大运河》(58cm×71cm)对光与色的描述即为印象派的典型之作。特别是19世纪法国以修拉、保罗、西涅为代表的“后印象派”更是把色彩进一步具体化,他们认为在绘画中应该把色彩的运用限制在红、黄、蓝、白四种原色的范围之内,这种重色彩理性分析与科学原理(他们以法国化学家舍夫略里的科学论著《色彩对比论》为座右铭)的做法,势必导致画家创作情感的丧失,最终使画面往往给人以冷漠和静止的感觉。这种理念也是与中国绘画的审美境界和所追求的意韵截然不同的,如果把法国印象派优秀的艺术因素植于一个新的增长点上,再向前推进一步,杨延文最终采用的策略是用中国绘画精神内涵去覆盖印象派的形式主义所造成的“冷漠”和“静止”。
杨延文由油画而进入中国画,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抛弃什么而拿起什么,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属于自己个性的绘画表达方式,他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放弃油画,而是改变了工具的性质,改用画布表达东方思维、境界的方式。艺术是相通的,都是追求尽善尽美,油画、国画的区别,只是通过不同的工具表达人类最深层次的思考,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两坡攀登喜马拉雅山,登到极峰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在他的绘画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审美特征:
其一,抽象的色彩意识。在杨延文的绘画中,色彩的运用是西方印象派绘画的红、黄、蓝三原色与中国传统绘画的黑白二原色的交融与辩证。西方油画中对色彩的描述是借助具体的对象来实现的,杨延文把它转化为一种抽象的色彩概念,在绘画中,他的红、黄、蓝三原色失去了依附的具体形象,这种审美取向是他对色彩与形象的总结和概括,他笔下的形象中有色彩,色彩中同时又具有形象,这种对形象的模糊处理是他对中西方绘画语言的高度驾驭,为画面增添了无限的品位空间和欣赏审美上的联想与想象。这最终来自他对于东方文化隐喻观、境界观、神秘观的追求。1983年,他那幅饮誉世界画坛的《江村疏雨》,实际上是他把东方的绘画艺术向西方画坛的一次成功推荐。在艺术的道路上,依他的个性,绝不会在西方艺术之后亦步亦趋,他就是要用东方的审美理论解释西方艺术。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山水画而言,黑白二原色是中国水墨的最高境界,是色彩的两个极端,西方绘画一向认为色彩针对于黑白是一种进步。杨延文的色彩观也正是以中国传统的黑白体系为基础的,他用黑白处理明暗虚实,用色彩渲染热烈的创作情感,在色彩和形象之间架起一道作者主观性个性化的彩虹,色彩是形象的色彩,形象是色彩的形象,使色彩的抽象性在东方审美情趣中有了一个统一的理念指向。他的画面是一个斑斓空灵的心源世界。
其二,平面空间的立体架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可游”“可居”和“三远法”都是纸上生存空间的幻化。较早的山水画作品,如展子虔的《游春图》和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都是对自然场景和历史事件的描绘,体现了人们最朴素的空间意识;泼墨山水的出现到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山水画才进入“寄情”“言志”的空间,“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泉石啸傲”的精神追求。遗憾的是,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他得之北方山水的一家之言“三远法”却桎梏人们上千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延文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在平面空间上架构立体的质感,赋予千百年来几至“穷途末路”的山水画形式以崭新的审美内涵。在山水画中,无意义的留白不是空间意识,空间应该是实际景物的另一种形式,实际的景物则是空间的具体与延伸。空间感的获得是对具体物象疏密、有无的辩证认识。杨延文画面空间的再建立不是理性的星罗棋布,而是充满天真烂漫的情怀。过河架桥遇山开路,满纸壅塞间到处都是流动着的空间,饱满的构图扩张着无限的生机。西方绘画和东方绘画的空间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位中国山水画家的绘画空间往往也是他心灵空间的反映,是艺术感觉的流露,因此,在中国山水画的空间里过多地涵盖的是艺术家对自然环境的感悟和精神追求的心象。中国宣纸的规格总是明显区分着长与宽的界限,现在好像也没有发明正方形的宣纸,除非你要普及剪裁成那种样式,潘天寿先生画语曾言:纸头要么长一点,要么宽一点,不长不宽最难办。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窥测中国画尺幅与欣赏视角的关系,人们在欣赏绘画时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视角。
在欣赏者的视野中,画面就是在流动的。杨延文的绘画空间理念革了传统山水绘画的命,他把对大自然的认识和个人的艺术追求,把整体感归于一个平面空间上,他的画非“可游”“可居”者,他永远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你在欣赏的过程中永远也不会走进他的画面,你只能在他的画面之前,带着欣赏的愉悦按照你的想象去创造你个人的立体空间。他在平面上的立体架构就是这样完成的。所谓的平面空间是他的绘画空间。所谓的立体空间是你情绪上的一种反应。
其三,题材与表现手法的高度合流。一个画家拥有什么样的题材是他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做出的必然选择,杨延文的画笔永远也描述不尽的往往是那些颇富诗意的水畔、桥溪、小巷、庭院,还有一些域外风光、大河激流等等,但最精彩的还是那桨声灯影的水畔,支离朦胧的桥溪,幽静蜿蜒的小巷和情趣恬淡、一派生机的庭院。我惊奇地发现他这位典型的北方汉子的笔下却充满了水的睿智,画面充满氤氲润泽的江南气息,莫非他人生的阅历中与江南水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或了却不断的机缘?否则,这只能认为是对题材的选择是内心深处所向往,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抑或是他长期的压抑和疲劳之后,渴望回到的精神家园。杨延文的故乡河北深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偏南,当滹水、漳流之冲,内迩京师,外连齐鲁,为畿辅咽喉。当美丽的传说和这一切水边的风景消逝的时候,杨延文幻想中的一切是否闯进了他的梦乡和笔下,他对于题材的选择明显地具有他强烈的理想化色彩。画面中方石堆积的围墙,块面结构的房舍,山色有无中的渔舟……这一切我们都不可能在同一处地址找到如此风格统一的格局,这一切显然来自他的概括与总结。在题材的表现手法上,杨延文以一种全新的绘画技法打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以法造型的语言形式,皴、擦、点、染在他的画面上了无痕迹,他以面造型,在扫、涂、抹、划间寻找笔触的丰富性和由其所带来的偶然效果,处处显现出他意识流动的痕迹。在这里,景物的形质不仅仅是用笔来刻划和建立的,更多的是一种笔墨结合。他力求达到的不是传统山水画中的以题材为依托的地域性山水的差异,而是绘画审美上所要求的节奏与气氛。因为他所选择的题材是理想化的,所以在表现手法上他也不可能用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来实现对题材的驾驭。他寓无法之法于热烈祥和的画面中,以此来讲述他所经历过的生活和对生活的参与。很多的山水画家以出版一本关于山水画技法方面的专著为荣,视之为风格成熟的象征,其实这是最庸俗不过的事情,当然在绘画成果的经验总结上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果对杨延文而言,恐怕难以实现,他的画充满了意识、精神、理想、境界的诸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所谓的表现手法只能从感悟的角度去理解。因此,他的画没有重复性,就连自己也是如此。
其四,全盘西化与东方神韵的和谐统一。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派绘画中的光,是指有具体光源的光,影是光的一种效果,具体地说在西方绘画中光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出现的。很多评论家在谈到杨延文的绘画时,仿佛都没有忘记他绘画中的光影效果,但不能笼统地谈这个问题,中国山水画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画中的光,已不再是西方绘画审美体系的具体形象,他把光处理成失去光源,若有若无的一种抽象符号,这种光不是出于一个具体的点,而是占有着整个的绘画空间,根据画面的需要,往往随时都可能在明暗关系的对比中凸现出来,从而成为画面上最生动的一种效果,这种光来自于他的“心源”。杨延文的绘画在形式上全盘西化了,他的绘画没有一处是属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视线条为东方艺术之生命的线的理念,在荡漾着的彩墨空间里被彻底消融了。间或出现的线已非典型意义上的中锋用笔,而是作为物体的轮廓出现的,由此,他的绘画也将给我们习惯性的艺术欣赏带来一定的困惑,他不但革了中锋的命而且还革了工具的命,他的画可以用毛笔之外一切工具来描绘,那么杨延文的画是中国画家族的一员还是一个怪异的另类?当年刘国松潜回大陆,大肆兜售其“革中锋的命”时,仿佛他还没有放下“带血的屠刀”,他要割断中国画的审美情感与东方艺术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绕道香港或别的地方回台湾了。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论,虽然过多地得到了人们的误解,但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却讲述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我们在欣赏艺术时,并非过多地排斥其形式的语言,而看重的是它内涵上是不是尊重了东方人的审美情感。站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至高点上,杨延文采用疏导、融合的理念,在这种艺术形式的肌体上注重了东方传统艺术的精神和审美情感,真正地达到了全盘西化(形式)与东方神韵(内涵)的合谐统一。他的创作实践形式在某种程度可以解释近百年来美术史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现象。
杨延文的画是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在顺利延进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一座高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对于自己的创作实践,杨延文如是说:“我的中国画色彩、块面、构图借鉴了西方油画的语汇,但意境是中国的。比如《丞相祠堂柏森森》这一幅,在颜色的冷暖对比和整个构图的饱满上,都借鉴了西画绘风,但整体却是中国画的境界。另一幅作品《冰岛》画的是西方巨石借鉴了西方绘画的语言,然而另一主体——江水却用了中国传统勾勒水的技巧。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恪守艺道,不轻易誉人的吴冠中称许他:“杨延文像海绵善于吸收,又像一头猛兽善于进取。”
杨延文的画越来越让人感觉到,一位卓然大家,能够拥有一种独立的绘画语言的审美体系,在他的背后必定不是单一的绘画因素使然,他必定包孕着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超乎常人的兼容精神。一个思想狭隘且不能与时俱进者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杨延文的画是西方绘画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的中西合一的再造,从形象到印象再到意象到心象。他的画首先在形式上暗合了人类生理本能的心理历程,他的艺术是中国传统山水绘画的极限状态的精神放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