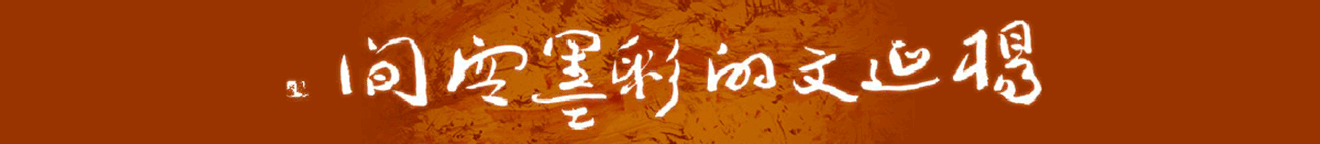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1/1/4 15:58:50 点击:1457
细读中外美术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殊而又普遍的现象,正统艺术在美术事业的运作过程中总是始集大成,继为僵局,所集大成的来头和所成僵局的突破,都有赖于非正统艺术家来完成。一部辉煌的人类美术史就是由这两部分艺术和艺术家构成的。
由此来审视我们面临的美术格局和预测未来美术运动的发展,让人觉得概莫能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熟视的美术史及其批评方法,总是有所偏颇。从形式上来说,他们不是倾向于前者,就是钟情于后者;而实际上,正统艺术的地位总是高高在上,非正统艺术总是处在从属地位一一这种从属地位又常常体现为美术史家从正统艺术的生发角度来解释与判断非正统艺术的历史贡献。这样,非正统艺术的历史地位便被定格在这样一个坐标上:在运作过程中被人横加指责,在历史的评判中,被人明褒实贬。笔者的上述议论生发于近日对大陆画家杨延文的思考中。
杨延文——一匹黑马
现在说杨延文是一匹黑马,对于读者,尤其是对于台、港及海外的读者来说,似乎有点事后卖乖之嫌。 杨延文自1978年进人北京画院任专业画师,特别是自1983年作品《江村疏雨》获意大利第五届曼齐亚诺国际美展第一名及金牌奖之后,不断地在香港等地曝光,展览不断,行情陡涨,声名雀起。但是,这匹黑马又是怎样的一匹黑马,我们如何从理论的角度来确定他的艺术的现实坐标以及如何来推测他的艺术的未来轨迹,却是一个尚未深究的命题。
杨延文是从传统艺术阵营中以非传统方式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杨延文1963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虽然他的老师是吴冠中,但是,他所接受的教育依然是正统的,写生是刻画,素描求结实,创作唯写实……循序渐进,一步一坑,何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今天,杨延文出外写生,他依旧是以清晰而流畅的线条勾画对象,部分局部甚至到了描摹的地步。但是,就是这个孕育于正统艺术子宫中的胎儿曾几何时挣脱襁褓,“哇”的一声,脱颖而出,一惊四座。他首先把苦学多年的油画束之高阁,突人堡垒重重、戒备森严的中国山水画阵中,拳打脚踢,硬是挣夺来一席之地。继而又劲装一袭,云鹤一声,长鸣而出,成为正统艺术、千百年传统的叛臣逆子。他以色彩与墨色的重叠来代替古人千锤百炼的效法程式,用流畅灵动的线条来描述心中的意象,或者说是描述心灵对物象的感悟,而不是用之来交代对象的体积与质感。抽象的表现包涵着具象的质量,造化的斑斓与意象的斑斓几不可分。
杨延文是从文化人阵营中以非文化方式,即商业性方式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也许是因为杨延文这儿年来较多地烦心于外部世界的认可,也许是他这几年来较多地获取了市场的认可,甚至也许是他的《江村疏雨》首先是作为商品走出国门的,人们几乎忽视了他的作品《翠屏织锦》曾经参加“建国三十周年美展”,并获得三等奖;他先后有作品参加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他的作品人选了1988、1989年摩纳哥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国际展、中日美术联展、美国克罗纳特博物馆主办的“现代中国画在美巡回展”等学术性展览。由此我们可以说,上述令一些画家自豪或羡慕的艺术经历被杨延文作品的商业性成功隐盖了,或者说杨延文作品具备的市场行情更为突出。这样,发生在杨延文身上的一些情况,得出了一个本来不能成立的结论,杨延文的成功方式是非文化方式。作为一个艺术家,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用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商业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无论你的作品有多高的艺术性。且不说郑板桥当年如何在传统文化范围内定位,也不说外部世界的艺术商业中所必须具备的艺术性内涵,就是从我们许多艺术家依然处在艺术探索为非艺术性因素干扰的尴尬境地,我们有理由认可杨延文的出脱方式是历史的必然。有趣的是,杨延文并不以此而面有愧色。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人们如今也在这条道路上有恃无恐地行进着。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论证杨延文以非文化方式冲破僵局的意义了。更何况,“存在就是合理”。
杨延文心中有一匹黑马
和杨延文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能“侃”,而且敢“侃”。真可以说是天赋口才,谈锋敢“侃”则因为他四十悟道、五十成名,在老而方盛、老而方可盛的中国画界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其实,真正的根本原因是他心中有一匹黑马!
去年夏天,笔者跟杨延文有过一次深谈,并作了一些记录,谨摘几段:
“我是从农村光屁股孩子长大的,我的个性是农村人,庄稼人的脾气就是直来直去。”
“别人是用理论来说明、证实、补充自己的作品,而我却是以自己的作品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或者说,我要用嘴、而不是用自己的作品来宣传自己的理论。”
“我不大羡慕别人,不超过别人我就不舒服。有人问我:现在谁画得最好?我说:我!人又问我:未来谁画得最好?我说:我!”
“在生活中,我想无拘无束,但不容易做到;在艺术中,我不想无拘无束却做不到,我是一个激情型的艺术家。”
“永远和别人拧着,这是我的思想,也是我的性格。今天你说白,我就说黑,明天你说黑,我就说白。” 杨延文的上述“宣言”,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概括,却不能用一个“狂”字来解释。理论批评的品性就在于冷静。
杨延文的“狂”是历史使然。他的祖上虽然也风光过,但到他的上辈儿,家道已然中落,靠种地维持生计。他是从农村闯进大城市的,他是靠自身的力量抢夺江山的,他完全有理由看不起那些家境优裕、家学渊博的公子哥儿。他自幼聪敏过人,悟性极高,他没有必要拿自己的前途,更不能抑制自己的创造力来迁就平庸之辈。如果因为他不善藏匿自己的优越、不善委屈自己而遭人指责,这决不是他的错,更不是他的悲剧。仰人鼻息过日子,在别人屋檐下躲风雨,决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是糟粕。自然,如果没有风险,人人都想当黑马。可是,不冒风险,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何以成黑马!历史的选择从来就是严酷的。
杨延文的“狂”是时势使然。千百年日积月累的文化传统,精华和陋习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千丝万缕,层层叠叠,窒息人,毁人。没有拿石头打天的豪气,没有一股子狂劲,何以冲破数十年非艺术铁蹄的野蛮践踏,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的现实氛围于艺术到底是乐土、还是困境,人以渗血的头额在前头开拓,自己在后头坐享其成,自然是怡然自得。可是,一旦你率先攀上高峰,先得一方蔚蓝的天空,先吸一口新鲜空气,他可却不是滋味,非在你脚下掏一个洞,让你一落千丈不可。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那些笑话别人有病的正人君子其实自己早已病入膏盲。
杨延文的“狂”是艺术使然,由“文如其人”推及“画如其人”,由“人品”论及“画品”,其间的逻辑关系被人为地强调了。这种强调,一方面是理论叙述的方便使然,一方面则是生活对艺术、特别是非艺术因素对艺术的驾驭需要使然。前者使艺术家追根溯源,得其所在,后者则使理论本身趋于简单化。正是如此,艺术家们被要求进入一个绝境:不张扬个性,便没有艺术创造,张扬了个性,便伤及一般社会学所要求的“做人”。所以,平庸的艺术家总是享尽春风,头角峥嵘的艺术家难免天折。就个人气质而言,杨延文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敢为人先、而不怕遍体鳞伤的艺术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在多数情况下只服从于艺术的需要服从于创造的需要,而较少顾忌。
需要强调的是,杨延文的“狂”是有根据的。创作上的“狂”立足于对艺术语言的锤炼,对对象的深入感悟,思想上的“狂”立足于对生活的思考,对思考的审视。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自然风貌,还是都市风情,都突出一个“韵”字。而这个“韵”字又寄藉于他对对象敏锐的感悟和对这种感悟的独特表达,因而展示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他喜欢用流畅的线条确定一定的块面,并由此确定块面与块面之间以及块面之外物象的构成关系,稠密而闪烁的色彩与浑厚而灵透的墨色相互渲染,相互渗透,相互晕化,创造出一个个意象天然但又别出心裁的境界。更值得推敲的是,杨延文近期的作品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定的过程感。这一方面是他在线条的运用上既着意于力度,又留意于速度。不仅通过短线之间或疾或徐、或轻或重、或光或毛之间的对比,而且,甚至主要是通过长线本身的运行变化来体现一种他人作品中不多见的过程感,从而具有较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既是一种语感,也是一种美感。这便是杨延文所说的:艺术作品应有“未完成感”。他认为,艺术创作要做到常画常新,就必须在作品中留下一定的人所不明而自己心里有数的“遗憾”,完整没好画,好画不完整。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就是释放,是释放的结果,更是释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延文是一个明白的艺术家,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
杨延文告诉笔者,他画画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少。笔者问他,思考什么?答日: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他认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最捷近的就是最好的语言。所以他常以尖锐的词令让人下不来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仔细推敲。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那些楞头楞脑的语言,才体现思想的锋芒,否则,何以一鸣惊人,何以刺刀见血。那些委婉的语气,那些体面的辞令,那些四平八稳的观念到底是思想的成熟还是为人的成熟,这种成熟与平庸又有什么区别,与虚伪又有什么区别?
文化的陈腐就是因为文化太成熟!
社会的僵板就是因为社会太成熟!
历史的滞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历史太成熟!
文化的更新,社会的进化,历史的跃动,最需要的就是黑马奔涌!
然而黑马难得!黑马难为!
写到这里,我想起前不久自撰的一副对联“闲云野鹤无根水,世态人情管他娘。”虽然有些粗鄙,但却是忠诚的。想到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但很少有人使之脱缰而出。
1993年4月13日于问梅轩
邵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