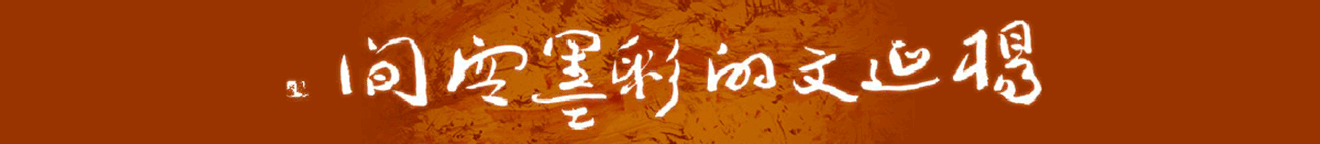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1/1/4 15:46:14 点击:1416
杨延文1938年生,河北深县人。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现为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北京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中国美协艺委会委员。
杨延文题画时慨言:“从艺真是个苦事,”余有同感。我大概写过几百篇评论文章了,仍感为文之难之苦。一则撰文如同绘画。重复套话必无味,二则评论如画像,必以写其心鹄的,正中古语“写心唯难”,三则文债过多弦绷得过紧,不可能“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那般地不受促迫,四则己有黄苗子、吴冠中等大家为延文兄“画了像”,后为文者还有多少新鲜的话要说?未开篇先就怯了阵……故语文谓之“试写”,不然真无从下笔。如果想偷懒,他未必不好写。我读了杨延文的许多画,看了有关他的许多资料,又听他侃了两个半天,在意象里只留下了“疙瘩延”和“铸剑堂”六个字——前者是长辈对他的爱称,后者是他的堂号,其实他的人生和艺术都浓缩在这六个字中了,他也以这六个字塑造自我。如果我是个书法大家就只给他写这六个字,将远较万语千言传神,岂不快哉!可惜我不是写“少数字”的书家。尽管我崇尚“写意”、“意象”,“一以当十”的美学,但我却不是这样的诗人或画家,这大概是艺术家与史论家的区别。如果那美术史可以用“少数字”来“意象”一下,也就没有了美术史,不过史论家也有自己的主体性,所以近年来,我时常在评论中插入些自我,为了享用一点为文的自由,也为了走近我研究的对象,若扯远了拉回来就是。
一、天生一个“疙捂延”
延文兄告诉我,他出生于冀中平原深县的柏树村,是父辈七人之后唯一的男儿,且落地就有“胎包”(按:他自己也说不清何谓“胎包”,故笔者不敢确认就是这两个字),人呼“疙瘩盐”,即宝贝疙瘩,说他命大,有福。也许为了香火传续,他这一辈就起了“延”字辈,后来“疙瘩盐”便成了“疙瘩延”,并为此专制了一方印。这爱称源自乡俗,宿命中有祝福之意,但一位画家以此为别号,一再地题署铃印于画,除了纪念之外,别有一番自信。自信,甚至自信得有点“狂”,自呼“人中龙”(印文),这正是杨延文的性子,不自信,就没有艺术史上的杨延文,杨延文这三个宇就不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
杨延文本是武将之后,根在金陵,算起来是明成祖朱棣御前武官的第二十世孙,其高祖为江山浴血战死于洛阳桥,所以以杨家为大户的柏树、也便有尚武习文之脉,不过他没有“延武”,而“延文”亦非偶然。据说,柏树村家无白丁,男人必须读书,起码在三年私垫以上,至杨延文的父辈虽然家业已败落,而文脉却不息,延文得以读书且聪敏过人,数理与文思兼优,自小学、中学至大学成绩不下前三名与杨家的文脉和“疙瘩延”的才分当有必然联系。艺术是才、情、功夫的聚合物,我坚信,没有相当的才气不可能成为大艺术家,我同时坚信文脉的遗传性对于文化创造的意义,笔者喜欢探究艺术家的家世亦缘于此。在杨延文的家世里,根在金陵使人想到他的聪颖,生于冀中又使人联想到韩愈那“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名言,杨延文无疑是位聪明人,也是一位多情人,当他日后自觉地意识到这南北文化的差异时,又对他艺术风格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寻新途别有洞天
吴冠中先生是位大家,能以极简的文字道出艺术真谛,他给杨延文画集撰写的序言全文是:“路是鞋底走成的,用我们自己的脚在自己的土地上走出小路,小路通世界,终成大道。——延文共勉。”
吴先生所说的“小路”是他和弟子杨延文共同的艺途一一融合中西的艺术道路。这原本是条“小路”。明清之际,西洋画传人中国之初,只有少数画家操此小道,无论是洋人郎世宁,还是郎世宁的中国弟子,由于西画自身水平和对中国画理解深度的限制,当时这融合中西的新派仅限于焦点透视在描绘楼台殿阁中的运用,以及光影明暗的立体造型对肖像画的影响,其后岭南画派(当时称“折中派”)的高剑父等人“专努力日人参酌欧西画风所成之新派,稍加中土故有之笔趣”,其着意点多在空气透视;自徐悲鸿直接到西方学习西画,他和蒋兆和、李可染、李斛等将西画造型与传统笔墨相化合,这中西融合之道遂在写实主义的造型意义上渐深,林风眠又从色彩的角度“调合中西艺术”,遂将中西融合进深到色彩表现的层面;近年,吴冠中、周韶华等人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点、线、面之构成,以水墨、色彩为媒介,挥洒出中国画的现代式样,融合中西的艺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百多年来,一条“小路”终成大道,更有杨延文这样的一批生力军加入进来,沸沸扬扬于中国画坛,堂堂正正地走向了世界。尽管他不能代替齐白石、黄宾虹对中国画传统自身的拓展,也不能代替董希文、罗工柳对西洋绘画的直接运用,但它确也不能被中、西艺术的单向演进所湮没,无疑具有骡子般自身的健力和新异、审美品格。尽管走在这条道上的艺家遭到过“不中不西”、“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甚至“混血儿”之类的非议,而他们的旗手却坚信:“将西方艺术的高峰和东方艺术的高峰相糅合在一起,才能摘下艺术的桂冠,登上世界艺术之岭”。
正是在文化史必然展现的这条上,在前辈们不计成败的探索基础上,冒出来个“疙瘩延”,仿佛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味道,美术史将拓展这条道路的重担寄托于延文和他的同代人。杨廷文也有这个机遇和条件,自四岁开始练蝇头小楷,在中学时代初具中西画基础的他,1957年考人北京艺术学院,恰恰投师于吴冠中门下。吴冠中说:“我这个当年的教师本来就是希望勇猛的年轻一代敢于声东击西,闯人艺术的不同领域,不服工具性能和表现程式的捆绑。”这话恐怕也早种在了杨延文心里。有人说启蒙名师是终身之父,有人说机遇和巧合是天生的福分,这些极普通的哲理再一次在杨延文的生命途程上得到验证并闪耀出灿烂的火花。从预科到本科六年间,杨延文同时成为吴冠中、赵域、张安治、高冠华的爱徒,在更高的层次上夯实了中西绘画的地基,尤其于素描和色彩方面展现出成为一位油画家的才能,吴先生夸他“杨延文的画,六十度的白干就是六十度”。可见他西画修行之纯正与醇厚。1963年,他的毕业创作《雁翱队》是油画,毕业后的创作仍然是油画,以及连环画,还有“文革”中特殊需要的美术字,仿毛体书法。时尚一度延误了他的行程,是新时期的春风唤醒了他的艺术理想。
杨延文色彩感觉好,并被北京画院看中。1978年正式调人画院,人们都以为他要去油画组,但他却出人意外地选择了国画组,不惑之年的杨廷文作为教过哲学的他已经有了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习惯,十分清醒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并认真研究过取夷之长、中西融合对维新变法的意义以及不少前贤由油画转向中国画的现象和这现象隐含的哲理。在访谈中,他向我阐述了“两个不行”和“两个无限”论,他认为,中国的绘画全走西画的路不行,全走传统的路也不行,而立定要走一条中西结合的路;传统的营养无限,西画的技法也无限,创造新的艺术样式正是他们无限的未来。他自己也坚信兼具中西绘画基础,正是实现艺术转化的条件。在众人的疑惑中,杨延文默念着《红旗谱》中他那位“老乡”朱老忠的名言“出水才见两腿泥”开始在宣纸上用油画、水彩的方法直接写生,俨然造出了一个新样。刘迅说:“这样的国画多新鲜啊!”石齐说:“小杨的贡献就是国画还可这么画。”他从前辈和同道的肯定转化为自我的肯定。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仿佛看到了创造新途的人们在互相鼓励中形成的合力。
杨延文“破釜沉舟”改画中国画的时候,我正从画画改学美术史,并以融会中西的蒋兆和为切人点。蒋兆和1936年由京返渝探亲,仿佛做了一个梦似地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油画箱,以西法作水墨人物画,一步就到了位。由杨延文的一鸣惊人我想到了这事,才气和灵感在思维转换的关键时刻会催化出一位巨人,而巨人的成熟仍然需要久久为功。
三、十年磨剑悟我道
杨延文自署“铸剑堂主人”。文史颇佳的他自然是典出有源。十年磨一剑喻宝剑所需磨砺之功,莫邪投炉助干将铸剑的传说更寓有一种栖性精神,所以那干将的妻子莫邪便成了宝剑的代称。
任何一门艺术或学问的深人慨莫能外地赖于铸剑般的苦功和研究,融合中西的艺术家可能更需要一个如同创造新合金那般的化合过程,更何况徐悲鸿、林凤眠、李可染、蒋兆和、吴冠中们的探索也没留下《芥子园画传》式的程式,重视创造性使他们都好像从头开始似的各造着自己的剑。选择了中西融合的杨延文也必须另造自己的剑,一把新样的合金剑。这大概是新派与传统派思维方式的自然差异。在传统自身基础上的创造几乎都有一个从“无我”的临摹到逐渐脱出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临摹一写生一创作的思维模式;而中西融合者,往往是在以往中西绘画基础上直接进人写生和创造,然后补传统。杨延文属于后一条思路。当他确立了中西融合之途。也就是决意不以单纯的金属,而是以合金铸剑的时候,他首先需要分别地研究相剖析中西艺术这两种元素,进一步探讨他们合成的可能性。他发现了中国画笔与墨的优长,又发现了传统在色彩和水分方面的余地,并发现了西画色彩、塑形、构成的可融性,从而确立了以色与墨、线与面的结合为突破口的艺术操作。杨延文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铸剑人。
杨延文重战略,亦重战术,因为艺术中有“术”。中国画在唐之前以色彩为崇,宋代发生分化,此后,水墨为上成为主流样式,色与墨分了家。杨延文的第一个战术就是要向这就近的主流挑战,就是要色与墨说话。他为水墨中的水增容,增加清染层次,让墨统领全局,然后以嵌色为主,让色彩在墨海中跳动起来,歌唱起来又或者将沉淀色调入墨,使色与墨水乳般地交融。当中国画的墨韵、西洋画的整体感、色彩的亮度和情感性融为一体火红的乡间小调,便在色与墨的交织申产生了异样的魅力。他以色与墨的交响塑造了自我,如果说他的墨是大提琴,他的线是小提琴,那色彩就是亮丽的小号,一任他这位指挥调度。
中国画以笔线节奏为长,西洋画以体面结构为优。杨延文的第二个战术是要将线与面接榫。他将体面揉入墨块,叉以竭笔勾皴相参,不仅使笔墨趋于丰富,也将山石、建筑的体量感和自然物的线的律动构成了新的交响。尤其他笔下的建筑、藤蔓之类的生物,西画的体面意识与中国式的墨气,西方现代绘画的抽象形式与书法用笔的毛涩、金石味巧妙地铸于一“剑”之中。
当杨延文找到了自己“多层面”的新术,则反复的演练,既为了升华他那“术”的质,也为了强化自己独特的性。我问“废画三千吧?”他说:“废画何止三千!”经历了第一个十年,杨延文的合金剑已在画坛熠熠闪光,在第二个十年,铸剑堂主人像老师吴冠中期望的那样,“正从空灵转向沉厚、质朴”。吴先生还提醒他这位“感觉敏锐”、“悟性高”的老弟子“重视三千年结蟠桃的神话”,把“十年磨剑”的计划放得更长远些,为了收获更醇美的蟠桃。
杨延文在铸剑中善悟。他在读传统书画中补传统课,也研究他崇拜的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又像李可染那样研究凝厚的传统画家黄宾虹,研究他的左邻右舍,但他更重视精神上的师承,在方法上却尽力地躲开,仿佛可以称之为“师法求异”的治学思维。当然,他有他的偶像,他对我讲有三位老师的话使他受用终身:一是王国维所说“天分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这位根在金陵、被南方画家归人南方画派的北方人意识到这一层,不仅在艺术中发挥他同时具有的燕赵豪情,也着意在沉厚、质朴上作文章,甚至于有意地“脏”,使聪明不致流入圆滑与浮薄;二是李可染所说“人为的景一定要扩大”,他领会其意,注意将人造物融人博大的自然,以造天人合一之境,以扩大造型的张力;三是吴冠中对他的评语“六十度的白干就是六十度”,始终提醒他保持艺术的浓度与纯度。这三位大师的三句话涉及到个性塑造、山水造境和艺术品位,成为他铸剑的精神法宝,并成了他豪放中有精微情脉、满密中见简约灵透、潇洒灵动中寓生涩质朴、苍苍墨海中色块斑斓的独家风格。客观说来,他主要倾向于飘逸潇洒的一路,为此有意地注意了方与圆、柔与刚、润与涩、灵与厚等对立统一的关系,但观画者往往又有自己的分寸,笔者就希望他的剑再凝厚些,再苍拙些,也许这是铸剑堂的宝刀进入老境的事,顺其自然吧!
四,造境畅神意翩翩
王国维论词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认为美术亦如是,笔者有同感,以王国维为师的杨延文可以看做是“境界说”的实践者。他在写生中造境,在造境中从自然之法则,兼有理想家与写实家的风采。不过,他更崇尚造境,可以说是由写境渐入造境者,或者说是未曾脱离写实的理想家,不离乎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他以理想、浪漫、造境为宗、又在写实与理想的中介点上,不同于以西画色彩为本的林风眠,不同于以笔墨写实为主的李可染,也不同于以形式美的抽象性为特色的吴冠中,他有他自己的坐标。
造境倾向于浪漫,倾向于形式,亦倾向于主体,倾向于道情、言志、写意、畅神。倾向于造境的山水画家将自我融人境中,以至物我两忘,达于天人合一。杨延文是位燃情的山水画家,别看他平日里那么潇洒,但作画时却墨饱色浓十分地投人。他热恋着生他养他的土地,“古来田园诗意浓”也成为他的情结,在乡野升起的那缕微妙的炊烟里,在农家小院里缀满的亮丽的辣椒、瓜豆中,寄托着这位自谓“河北佬”的乡情。江南水乡仿佛是他梦中的祖籍,他爱那黑瓦白墙、础石垒垒的民居,爱那些镜子般流淌着音乐的小河,爱那富有人情味的小桥和渔舟,像含情脉脉的抒情诗人,在月光、倒影、轻烟里,为观众留下咀嚼的余韵;有时像慷慨激昂的壮士,古树和着大风,浓云伴着故垒,为屈子树一面纪念碑,或高吟一曲“风潇潇兮易水寒”,苍凉里寓有悲壮,而这种豪情是时常直入他多次喧染的倾斜走向的云天里去的。
杨延文重情,他在题画中说:“任何人都离不开师承,其中当以继承师之用情之处最重要。”他画静物,似林风眠的厚涂法,但情却是自己的。如《刺头开花》一幅题道:“刺头开的花最好看,写我对仙人掌的印象”,又道出了一番有我之境。杨延文艺术的独特性就在于此,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脱师,从内美的角度而言,也要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此方为真情真画,他自己不就是一朵不类寻常的“刺技”。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他的路,他的技、他的情分别的做了叙述但读画时常常分不太清,景语都化做了情语,情语又转换为笔墨。他以情趋遣形式,那中西结合的形式也最与其情相合,最令其神畅达。当然这一切又并非都是预设,而是常常在笔墨挥运中爆发出灵感的火花,激发出千变万化的趣味,那语汇与造境、畅神已浑化为一个整体。当我看到他的《午后曲》,恍如山峰般的墨团竟然是一架钢琴的时候,我想他作画的情状是一如画中的乐手那般陶然,甚至于他就是那乐手,并不按照乐谱来弹奏,而随着那草原上的风云即兴挥洒。才子型的敏悟者杨延文有这本领,当他进人“游于艺”的境界时,他就是那乐曲的主宰。
杨延文逾六十了,正当收获的季节,但他好像仍是一位翻翻少年,潇洒、爽朗、乐天、充满着朝气,因为他的心不老。我也相信,他会是一位永远年轻的山水诗人,会把那融合中西的火炬燃得更加璀璨。同时我也认为,融合中西的艺术家们比起单向的中国画画家或西画家将面临更大的难题,他既要分别地吃透中西两座大山,还要研究如何将这两座大山的精华融为一座新的山,而不是把两重山山头削平。这新山的质将取决于对中西两重大山分别研究的深度,也取决于铸剑人化合的技巧。正因为中国画和西画分别的无限性,也决定了中西融合的无限性,同时提出了将融合中西的道路不断推向新阶段的使命。杨延文说,艺术的极致永远达不到,又要永远地追求极致。我想,艺术原本就是追求那永远达不到的极致,或者说是对那永远达不到的极致的追求。这就是我所知、所识、所期、所试写的“铸剑堂主”——“疙瘩延”。
戊寅初秋撰于散心
刘曦林